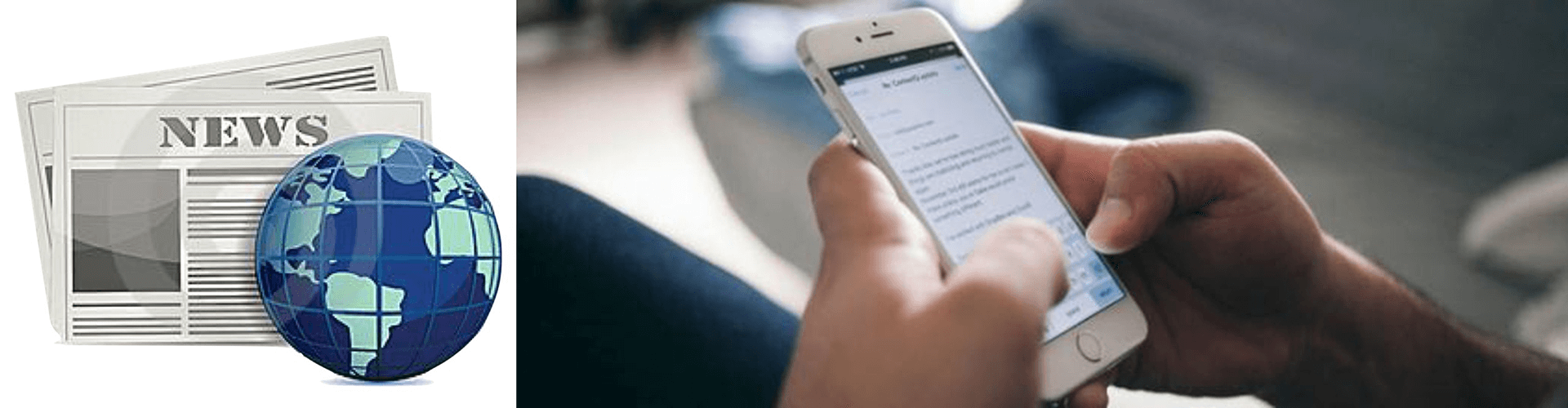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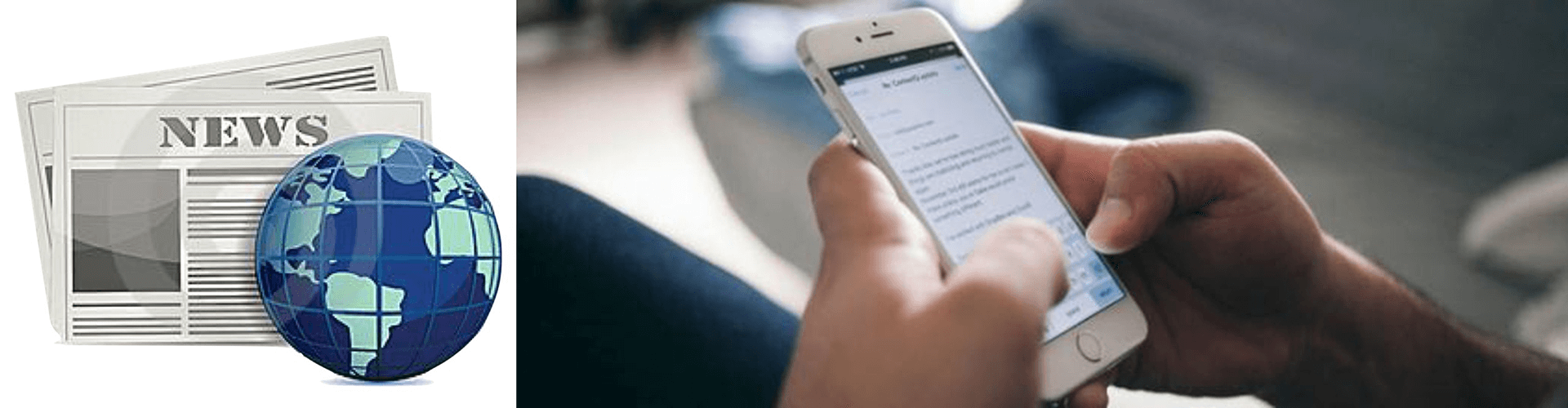
11 月 14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支持,北京甲子光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主办的2020「甲子引力」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
探客柏瑞联合创始人兼 CEO 林思恩博士受邀参加出席大会,参与前沿科技专场「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圆桌论坛,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蔡茂林、中科院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山世光、起源太空创始人兼CEO苏萌、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小燕等业内专家,共同回首 2020 年的科学大发现、提出科学畅想、探讨学界与工业界的碰撞等热点话题。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一甲、蔡茂林、林思恩、山世光、苏萌、朱小燕
以下为圆桌论坛实录,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张一甲:首先,请每个人先介绍一下自己。
蔡茂林:我一直从事机械电子工程领域研发工作,在海外学习工作十年,也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研院院长,最近五年,我们团队在无人机、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业项目也获得了一些风险投资。目前,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科技与产业的融合正在加速,我们也是见证者。
林思恩:跟蔡老师不一样,我是2011年博士毕业以后做了很多产业化的事情——2011年至2015年,把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技术方法落地到中国第一个神经科学产业化应用公司;2015年到现在,把技术应用到教育。
对于今天的主题,我想法还是蛮多的。我们一路上需要持续不断的前沿创新,同时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产业化应用落地,有很多科研领域未必有的数据,所以说基础科学和产业应用双方都需要互相依靠。
山世光:我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山世光,从计算所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做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所谓计算机视觉,旨在给我们的机器、AI系统安上摄像头等眼睛,使之像我们人一样去看,看人、看世界,理解人和这个世界,显然人工智能很多时候都需要这样的功能。
除了做研究之外,在四年前我也和我的学生做了一个公司,希望把计算机视觉能够应用到产业里面去,尽管现在看起来技术落地很不容易,但确实是值得去做的事情。非常高兴可以聊聊基础科学,谢谢大家。
苏萌: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家小行星采矿公司起源太空的创始人苏萌,我也是银河系最大结构“费米气泡”的第一发现者。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和一甲是北大的校友,今天上午一甲在大会上的分享,最后她讲到《生命3.0》这本书,《生命3.0》的作者就是我的导师,在美国十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切身感受到不管是认知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太空时代真的要到来了。人类需要具有太空能源和资源的公司出来,成为我们人类未来革命发展的重要基石。
朱小燕:大家好,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介绍,我的经历跟蔡老师有点像,我是在日本获得的硕士和博士,1993年回到清华,之后在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刚才苏总问我为什么创建这个实验室,这个绝对不是我创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1987年就筹建了,那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筹建的重点实验室之一,那个时候国家开始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1993年作为一个成员参加进去。
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实验室的老前辈,最早是在1958年就开始做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那时候的通讯、信息传播和的速度现在没法比,但前辈们跟国际发展还是挺紧的,我们实验室30年了,我也做了差不多快30年了,一直做的是人工智能工作,这几年AI突然被炒火了,问我有什么区别?就是累。但有人支持,有经费那是好事。
五年过去以后,大家开始考虑人工智能怎么落地?真正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科学的研究,现在还很少。这几年突发猛进的都是技术,如果技术不落地,会带来厄运的再次发生。如何避免呢,全靠做研究和做产业发展的人共同努力,如果技术可以落地,寒冬来的晚一点或者是浅一点,很快就腾飞起来。如果不落地,就会再次被人垢病,成为一种假、大、空。
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会议的题目非常契合,研究和产业怎么更好的融合?它是互补,如果产业做不好,技术研究或者是应用基础研究也一样会砸锅。没人用,就没人出钱,没人出钱,自己就没心情好好做了。因此,技术或者是研究必须支持产业,支持行业、产业发展。反过来产业的需求也是对技术发展巨大的促进。希望这个会议能跟大家好好讨论讨论。
张一甲:我的第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站在自己的学科视角给我们简单开一下脑洞,用最形象简单的话告诉大家,在你的学科当中最近一年或者是最近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突破性进展是什么?
蔡茂林:一甲的问题还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团队最近在非标机械零部件的数字敏捷制造上取得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进展。机械加工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行业,以前一个非标零部件委托给工厂时,产品交付基本上需要三到五天的时间。需要经历报价、工艺制定、排产、数控编码等,是由很多碎片化工作构成的。
这些碎片化工作都需要人来完成,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你把工作给了工艺师,他可能今天没时间,要明天下午做,就得等到明天下午了。总耗时几个小时的工作,切成五片,由五个不同的人完成,需要几天的等待时间。
对非常传统的行业,我们能做什么?用AI的技术,把需要五个人完成的工作全部用计算机自动完成,一个3D模型图纸上传到云端,实现自动报价、加工工艺生成、根据机床型号自动生成编码,把五天的工作缩短为几秒钟,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科研成果给传统产业带来的颠覆性进化。
工序中人的存在,让传统产业效率变得无比低下和不确定。如果我们用机器的算力和智能决策去取代人,产业还是原来那个产业,但工作效率将会提升一百倍以上。
说基础研究之无用,我在二十年前读书学习神经网络的时候,觉得真没什么用。今天,我们发现通过计算机算力的提高以及深度学习算法的进化,这些东西还是这些东西,但却变的如此重要和具有无比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跟大家分享。谢谢。

为什么今年马斯克发布小猪脑机接口成果以后,我们又把米格尔请回来,他做猴子脑机接口实验是很早的,但我们肯定主要不是看什么动物实现了脑机接口,而是看背后材料学的突破。

苏萌:太空科技这个领域大家总是可以找到很多热点,不管是马斯克还是我们国家最近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叫“天问一号”。太空这几年变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这个热点伴随的是科学技术突破和技术能力的进步。
朱小燕:人工智能有几种描述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是认知智能、感知智能、自主智能作为智能研究进展的不同阶段。
现在有一个预训练模型非常成功,很明确的训练数据的语义信息学习到模型中。就像我们读万卷书。应用时用具体任务数据进行微调,可以表现的很好。这个模型的前提是用了大量的算力,例如GPT3,理论上GPT3和GPT2只有工程上的提升。但是,GPT3拥有1700亿个参数,模型训练一次,花费一千多万美金。
咱们先不提这是否是大家都去追求的途径,但这是一道让我们看到了机器能够学习很多东西的曙光。理论上把所有的书都让机器看,机器就能做各种各样事情了。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变的更简洁、便宜让大家用起来,这是需要进行做的另一个突破。
另外还有一个,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人机交互越来越受到重视,机器和人或者是跟环境交互。机器如果不跟外界进行交互,机器的智能就是一种伪智能,是可编程实现且一成不变。现在国际学术会议,跟机器人相关的竞赛,没有人机交互的环节,这个比赛都不合格,或者一个团队的作品没有人机交互操作没有资格参赛。
例如机器人魔术,不是变个魔术就完了。例如,瓶子盖着盖,手滑一下东西就进到瓶子里,不行。一定要说人跟机器用语言或手势共同完成,才可以。
机器有智能,一定要知道这个房间黑,那个房间亮,这有一个楼梯,有什么事跟人讲,只有这样做才有点像科幻电影的智能。根本上还是知识,比如机器想要出门,你想告诉他门在右边,怎么可以让机器听懂你跟说的话?现在有很多人研究这些。
张一甲:我们都知道科学的进展就像知识树一样,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叠加树枝,树枝到树干不断往外长,后来人到末端的突破就越难,也会有很多很悲观的声音,有本书在科学的终结,爱因斯坦之后,人类的天才已经没有了,也有很多声音说在基础科学领域现在好像发展的越来越慢了,我想站在外行的角度问大家,基础科学发展的速度是在变慢吗,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评价我们基础科学的发展速度快了还是慢了?
这周新闻发布的谷歌量子计算机,仅仅用了短短200秒,就完成世界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花费1万年所需的计算量,这真是一个堪称“恐怖”的计算速度!这将带领人类可以认知到更多的未知世界。
人类的认知水平,往前看一千年、两千年,也许差不了太多,包括暗物质、多维空间等,我们现在的认知仍然是有限的,量子本身我们也不清楚它的机理。但是,现在的数十年,人类获得的知识是在爆发式增长。
因此,我的观点是:第一,认知是无限的;第二,人类认知的速度在加快。
林思恩:在座各位专家的专业方向都是有人工智能底层的逻辑,人工智能作为底层逻辑有算法算力数据,在我经历的所有行业里,也都有算法算力数据匹配的过程,这也是特别好的评估基础学科发展速度的方法,通过看哪个强、哪个弱就可以。
山世光:我的感觉,不是基础研究变慢了,而是重要基础研究的成本变高了。
很显然,基础研究的进步是有节奏的,会有快速发展期,也会有发展缓慢的平台期。例如120年前,那个时候物理学界都觉得再也不会出现像牛顿一样伟大的物理学家了,因为他们觉得物理问题基本解决了,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很清晰了。结果没过几年,爱因斯坦就出来了,相对论来了,整个颠覆掉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以此观之,我们现在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也可能是大错特错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就一定对吗?未来也可能出现另外一个人,提出一套更好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颠覆掉,毕竟现在物理前沿还有很多的困境用当前的理论解释不了。
山世光:如果基础研究只是添加细枝末节,那肯定会越来越慢。但科学规律告诉我们,最重大的基础研究往往会重新种一棵树,彻底颠覆掉之前那棵,从而会有一段新的快速增长期。
我们真的是在进步,理解宇宙的技术在进步。但是光靠好奇心这个人类内心最底层的欲望推动的话其实对世界的理解是会减缓的,因为好奇心的成本太高了,谁来出这个钱?
我在哈佛的导师说天文学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三十年前是哈勃望远镜,现在还是哈勃望远镜,为什么?因为新的望远镜太贵了。如果说我苏萌做太空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公司起源太空能够利用好太空资源,能够为文明产生社会回报,那么这整个科学就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最近有报道,超导可以在常温下15°C下实现,原来是-260多°C。但是这个还是不可能实际应用,温度提高了,但是有高压要求。我算了一下,其所需压力是我们日常大气压将近一千倍。这个事再继续下去也许就有可能了。
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问题。超导这个材料能够在常温甚至是常压下可以实现,我们的轨道交通会是什么样?实际上肯定会有前人都没法想象甚至科幻片现在还没有出现的结果,我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挺好。